如果不信教,宗教就與我無關了嗎?研究宗教的人都要信教、都很嚴肅嗎?宗教學研究只關心那些在教堂、廟宇跟儀式裡的人們嗎?為什麼宗教生活跟理解這個世界息息相關?《時差 in-betweenness》第十二期播客從方方面面,談彌散在生活中,和歷史、文化、政治、社會不可分的宗教,宗教研究學者和宗教師從他們踏入相關領域的歷程談起。
【編按】本文內容來自《時差 in-betweenness》播客第十二期「宗教學:信仰,魔法,身份,權力」,C-Culture Zine獲《時差》授權刊登文字版。
主持人:
郭婷 (Guo Ting) 多倫多大學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對談人:
程曉文 (Hsiao-wen Cheng) 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副教授
李紀 (LI JI)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倪湛舸 (Zhange Ni) 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鄭利昕 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神務碩士 醫院宗教師
進入宗教學:傳統神學、宗教實踐到跨領域宗教研究
郭婷:今天節目開始之前,我想先表達一下沉痛的悼念,前幾天有一位宗教學界的前輩,台灣的林富士老師去世。我本來並不是研究中國宗教的,也不是研究傳統中國文史哲,所以並沒有和林富士老師當面見過。但是一直從他的研究中得到靈感,所以非常感謝他。這兩天也在臉書上,看到很多他過去的同事和學生對他的紀念。雖然學術界很多時候有失公正,但還是有些地方讓人覺得非常溫暖,就好像點亮一盞燈,而那盞燈一直會亮下去。
這一期我們來談宗教學,不只是談學界,也談它的實踐。線上幾位雖然都是跨學科的研究者或實踐者,但也都是宗教學出身。我相信大家在和別人介紹說自己研究宗教學的時候,通常會聽到幾個問題:你自己有沒有宗教信仰?你研究什麼宗教?以前還聽到的問題是,那你畢業之後做什麼,是不是準備出家等等。我以前經常會開玩笑說,對,以後出家、給人算命。其實不只是學界外,學術界不同學科對宗教學領域都有些陌生,因為它確實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學科。就我自己而言,我博士的訓練在愛丁堡大學神學院。愛大神學院作為一個新興科系,比較有抗爭和創新精神。設立之初就是為了和傳統神學或宗教有關學科對抗,所以它是無神論的、非常講究世俗化和社會科學方法。
我記得當時大部分系上的學者,無論男女都打扮得非常不羈。開會的時候,美國宗教學、尤其是聖經研究的男性學者都會穿西裝打領帶,但是英國宗教系的老師就穿睡衣或道袍,是非常不一樣有叛逆精神的學科。所以我們學科的訓練也是比較講究宗教和社會、宗教和當下社會的關係。我當時雖然是從AI人工智能進入,但也是專注於研究英國世俗化,。當然在神學院也會碰到其他科系的同學,比如傳統的舊約研究、新約研究、神學研究,也有一些道學博士(利昕訓練的背景)或是教牧學學位等不同的朋友。那想請幾位聊聊,你們的研究背景是怎麼樣的,跟大家聊一下心路歷程。
鄭利昕:我剛從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碩士畢業,這個碩士英文是Master of Divinity,它不是一般的學術課程,是比較偏實踐的,所以項目培養中有很多的實習、見習。我一開始申請的是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的M.A.,大多數人進去的時候,也都想著以後要讀宗教學或者相關學科的博士,而讀碩士是基本的門檻。
但是當我進去的時候,發現它有一個神務碩士(或譯道學碩士)的學程,比較偏實踐,感覺很有趣。在進去之前,我不知道學院內有這個學程,因為一般來說傳統上只有基督徒才會說要成為神職人員,需要讀這個道學碩士學位。
但我們神學院最近大約十年有一些變化,開始接受不同宗教的人進入神務碩士學程。所以我們班上基督教當然很多,還有猶太教、佛教、伊斯蘭教、印度教,還有以人文主義者。所以我也算誤打誤撞進入宗教學或宗教實踐的領域。
在進入神學院以前,我是學物理的,物理博士讀到一半發現「人生好沒有意義,我之後要去當碼農了」,所以想找一個有意義的專業。在探索包括哲學、人類學之後,發現我對宗教學最感興趣,但後面又發現我真正感興趣的不是宗教學,而是宗教實踐。或者說以傳統宗教實踐為啟發、一種比較廣泛的社會實踐形式。
郭婷:謝謝利昕,這是比較有趣的一個經歷。那我們來聽一下湛舸聊,湛舸也是芝加哥神學院畢業的,但你讀的是宗教學研究。
倪湛舸:正好是接著利昕說,我跟利昕在同一個地方接受宗教學教育,但我是讀完碩士去那裡讀博士。芝加哥大學的神學院比較特別,它其實是一個大的宗教學中心。像利昕剛剛提到的,芝加哥大學的碩士班也涵蓋各宗教,但也沒有全部含括。當年博士階段,我們有九個program,其實就像科系一樣。
除了剛才郭婷提到舊約、新約研究,這些神學院相對傳統的科目。在芝加哥大學更廣一點,還有宗教歷史,宗教社會學,宗教人類學,當年還有宗教心理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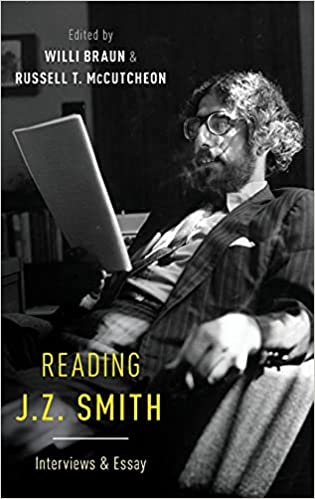

photo by The Chicago Maroon
在基督教之外,像宗教歷史,當年有J. Z. Smith等一大幫人他們什麼都做、什麼都比較,那個走向現在相對來說比較衰落、受批判,而後來這些年則有推動專門的伊斯蘭研究。我的專業當年叫做「宗教與文學」,現在叫做「宗教、文學與視覺藝術」,理論上包括電影、電視、電子遊戲。
剛才郭婷老師有說到,英國那邊可能比較狂放,其實芝加哥神學院也是一樣的,divinity school 和 seminary還是區別很大,不同學校的神學院風格也不一樣,芝加哥大學可能最偏向宗教學。相比之下,杜克、耶魯和哈佛的神學院更加接近於神學。不知道利昕有沒有要補充或更正的,因為我畢業十年了。
鄭利昕:我剛查了一下,現在的研究領域變成十一個了。宗教社會學現在已經轉變為宗教社會學與人類學。
倪湛舸:其實當年已經很有人類學的痕跡,我們當時都一定要讀Talal Asad,跟著Bruce Lincoln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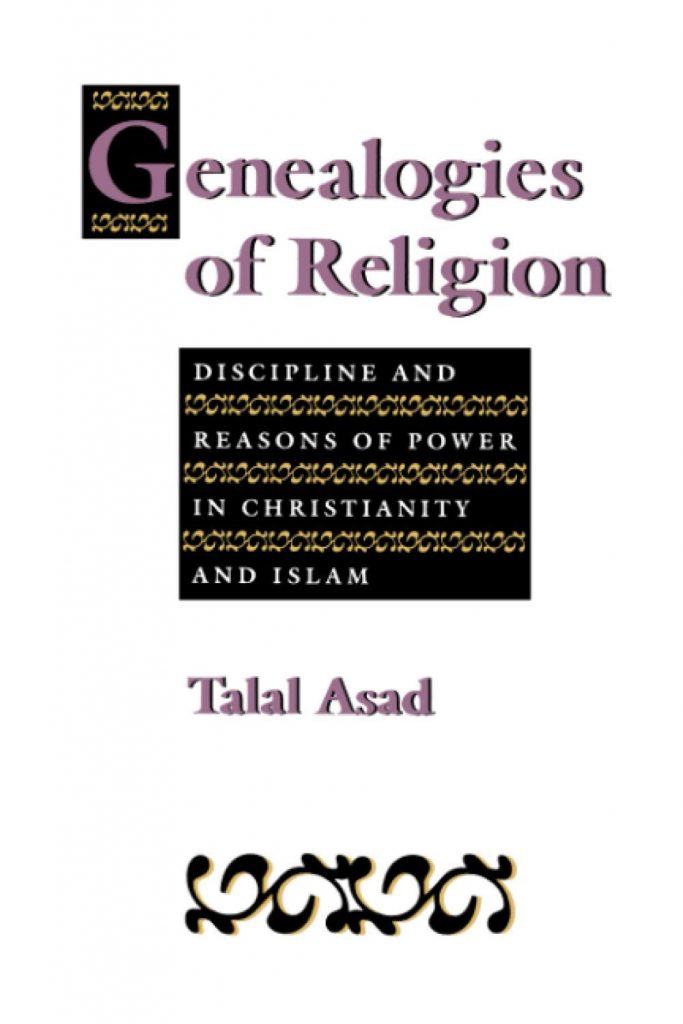
郭婷:芝加哥神學院確實有這個傳統,在美國以至於全世界來說,都是比較講究宗教學研究的傳統,是比較特別的神學院。剛才湛舸提到的這些學者,包括芝加哥大學的J.Z. Smith,對於學宗教學的人來說,都是最經典的一些學者。世界宗教學研究學會的介紹說:把宗教作為人類現象來研究。我覺得這可能是我們做宗教學研究比較奉行的原則。當然現在越來越多神學院也好、宗教學研究也好,會去研究「世界宗教」和不同的宗教傳統。在英國這兩年出現了一件爭議,我們當時神學院的本科課程,有一門課叫「世界宗教」,這種研究現在被認為是殖民思維的產物,就是說「我們有基督教,你們不管什麼其他宗教則是『世界宗教』」。這個概念現在非常有爭議性,學界還在思考除了「世界宗教」這個說法以外的可能性?
後來神學院裡面也有伊斯蘭研究,但是還沒有其他例如佛學等研究,因為佛學研究跟伊斯蘭、猶太教研究很多時候都屬於亞洲研究,這是現在仍存在的問題:區域研究和所謂正式學科之間的張力,兩者的區別是什麼?這也給學院派研究帶來很多問題。其實我們今天的另外兩位嘉賓,李紀跟曉文,她們的跨學科研究就匯合了漢學、歷史學、中國研究、佛學研究,這些其實是有交叉性的。不知道你們進入宗教學或者是進入學術研究的心路歷程是怎麼樣?
進入宗教學:宗教經驗、歷史學
程曉文:我大學念的是中文系。碩士班在台大的時候主修思想史。到美國以後,在華盛頓大學念博士班的時候是歷史系,跟Patricia Ebrey做宋史。真的開始披上宗教學的外衣,其實是拿到現在這個研究東亞宗教的工作。這個工作做著做著,仿佛也做起宗教研究,現在我每年都教跟宗教有關的課,我等於是 teach yourself before teach students。
其實我在大學時代是基本教義派、福音派的基督教徒。那在美國聽起來很可怕,但在台灣就是一個普通的基督教徒,也沒有太多其他選項。我以前非常認真,有參加我們大學很的團契,也會跑去神學院修課,還很認學習古希臘文。後來有一個過程,我慢慢不去教會,也不認為自己是基督徒了。但是我覺得非常可以理解宗教信仰,也認為宗教信仰是需要認真看待的。我自始至終都不僅是從社會學角度去分析宗教,宗教信仰可以讓我們重新思考很多做研究時被忽略的問題和常見的預設。
郭婷:大家如果有聽《新書介紹》(New Books Network)這個播客,曉文老師最近有一本新書,在播客上有段非常精彩的訪談,這本書是叫Divine, Demonic, and Disordered: Women without Men in Song Dynasty China(《神,魔,亂:沒有男性的宋代女性》),我不知道有沒有中文翻譯,直譯是「沒有男人的女人」。節目非常精彩,也講到學術訓練的心路歷程。也發現我們有一個共同朋友Donovan Schaefer,你們都在宗教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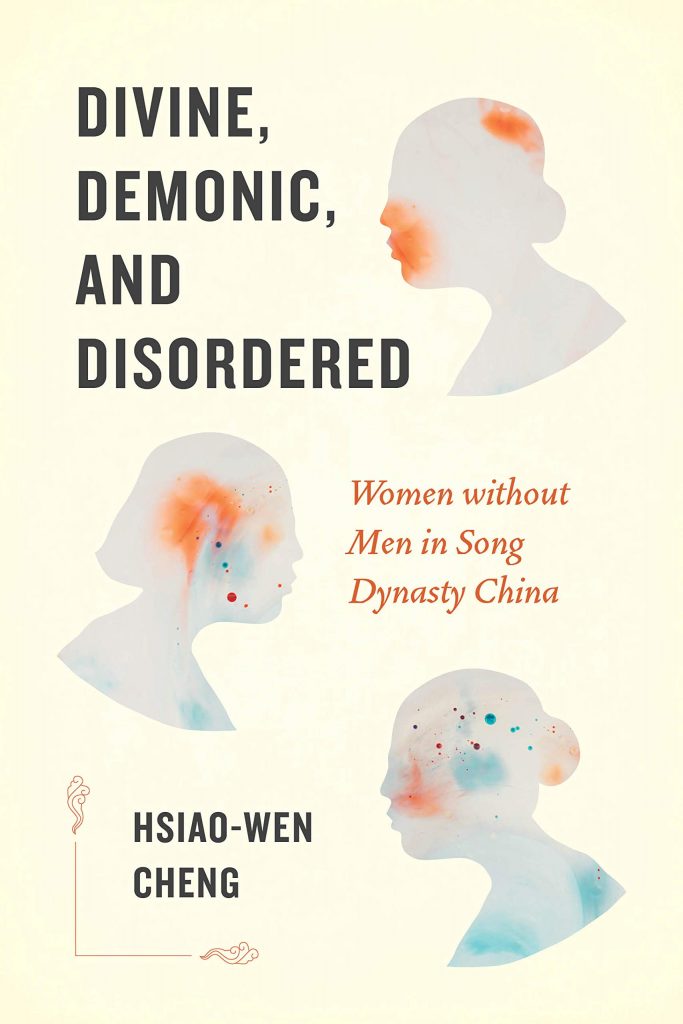
程曉文:我在東亞系,他在宗教系。但是當初我的職位是一個東亞–宗教研究的跨系招聘。
郭婷:原來如此,這也是我們這種跨學科研究者在找工作的時經常要遇到的問題,看似好像什麼都可以申請,但具體工作其實都要看機緣巧合、看學校的方向等等。你剛才提到以前在臺灣還是基督徒,還挺有趣,在台大是有自己的學生團契?
程曉文:不同教派有自己的團契,天主教也有。我的那個叫「校園團契」,在臺灣也是一個全國性機構。它的重點是做學生工作,在中學還有大學去幫學生訓練、組織等等。還有一個團契叫學員團契,性質類似,也是福音派。還有一些可能比較大的教會組織也有,比如「召會」(聚會所),它最早好像是英國某一個兄弟會的分支,和倪柝聲有關。反正有好幾個團契,我的團契在眾多團契中,那時候是思想比較開放,我第一次聽到女性主義就是在那個團契裡面,所以其實還蠻有趣。
郭婷:原來倪柝聲的教會在臺灣以這種方式生長。我前幾天還在看連曦老師的書,剛翻譯成中文在台灣出版,《血書:林昭的信仰、抗爭與殉道之旅》。我記得他之前有寫倪柝聲,《浴火得救》(Redeemed by Fire)。之前還看過另一本書,倪柝聲的家人後輩,已入籍美國,書寫他們家族歷史,那本書叫Shanghai Faithful: Betrayal and Forgiveness in a Chinese Christian Family,他的祖父林步基在上海讀聖約翰大學的神學院,做了林語堂的同學。而林步基的太太就是倪柝聲的妹妹。這本書寫到許多教會的傳奇人物,但在中國他們的命運可能就是被慢慢淡出。
我自己的感覺是,在中國接觸宗教和在臺灣接觸宗教不太一樣。因為在臺灣,宗教相對能見程度更高,學校也有不同的團契;中國大陸相對來說比較少見。當然2000年後半我讀大學的時候,相對來說風氣比較自由,還可以看到非常多韓國傳教士。很多研究宗教學的華人朋友,其實都是因為教會的關係而接觸到宗教。
可惜我不是這樣,大家都問我是什麼原因接觸宗教學,其實我是因為一個人工智能的問題。我本科讀的也是宗教學,有宗教哲學這門課,課上提到一個問題:如果一個人出了車禍,臉被燒毀,醫生給他換了一張臉,他還是不是他?就是人格同一性的問題。年輕的我就說「天哪!世上有那麼有趣的問題,我一定要研究這個」。當時就問老師,要研究這個問題,我應該進哪個學校,哪個科系?結果當時不知道誰,可能也是隨口說:「你應該研究人工智能,這是人工智能哲學的問題」,然後就誤了我。後來我申請學校的時候選了人工智能哲學方向,誰知道人工智能哲學其實非常理工科,我花了非常多時間去研究科學史和人工智能哲學,後來才漸漸進入宗教學領域。自我介紹的環節最後一位學者,請李紀老師來聊一下是怎麼從歷史學進入宗教學這個領域?
歷史跨入宗教 從法國大革命到中國傳教史
李紀:我的求學經歷很簡單,從本科、碩士到博士都一直是歷史系。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讀了本科和碩士,專業是法國史,本科畢業論文是關於法國大革命。當時我的老師是國內法國史研究權威,但他接受的法國史系統訓練還是傳統的革命史研究,那時宗教不在法國大革命研究範圍內。那時候接觸1990年代末在大陸非常新鮮的法國心態史、性別研究,覺得那就是我想做的。而且在做碩士論文的時候,我已經從當時的書籍、沙龍來處理大革命起源;另一方面也有年輕女孩對巴黎的想像、嚮往,所以我申請美國博士班的時候,研究計畫是「性別和革命的比較研究」。
到美國第一年,我在密西根大學歷史系,主要是研究歐洲史領域,還是想做大革命。我記得第一學期參加一個關於大革命的工作坊,遇到一位做法國研究的學者,他對我說,我聽說你想做法國大革命,讓我想想還有什麼議題沒有人碰過。當時才意識到兩百年以來,法國大革命的方方面面,從日常生活到議會,都被人研究過了。我非常震驚,而且相對於我的同學,雖然我也學法語,但沒有去過法國,沒有真正進入當地檔案館,因此我非常焦慮,想該怎麼辦。
學了兩年歐洲的各種課程,到第三年要開題的時候,我就想還是想做一個跟中國相關的題目。既然法語比不過人家,還是做一點能用到中文材料的研究,當時就看中法之間有什麼聯絡。從歷史上來看,傳教士肯定是一個很大的團體。

所以我就第一次去了法國。正好那兩年有一個巴黎高等研究院做書籍史的教授長期在密西根大學客座,我到巴黎的第一天,他就從機場接我到巴黎外方傳教會的檔案館。巴黎外方傳教會就一直跟隨我到今天,教授把我介紹給裡面的人,那是我第一次走進一個修院,而且是十七世紀的建築。它在巴黎第六區,旁邊是巴黎高等研究院,和Bon Marche百貨公司。進去以後,先是他們的小教堂,穿過大大的樓,進到閱讀室。後來我就一直在那裡,第一次去了兩個月,接下來四年基本上一半的時間都在巴黎。就慢慢進入宗教史,到現在我介紹自己的專業一般都說是宗教史或社會史,也涉及一些性別研究。
我剛才聽你們講,還是有很多不一樣,一個是我沒有任何宗教學或神學訓練,還有我一直做天主教,而且主要是法國天主教傳教團體在中國,屬於在華基督教史領域。研究天主教這種非常系統性的教會,尤其是在中國的傳教,那種路子我覺得是很保守落後、非常制度化。跟大家現在很fancy的談那種宗教、彌散(diffusion)、宗教生活很不一樣。 我在港大人文社科研究所,大部分做宗教的老師,都是做道教、民間宗教或人類學。跟他們在一起,我經常是唯一一個做基督宗教,而且是做天主教的研究者;聽他們的討論,覺得跨學科衝擊特別大。
系列文章(上):
【時差】宗教學(二):看見生活中的宗教 農村人眼中的天主教與漸趨多元的宗教師訓練
【時差】宗教學(三):去標籤化的同時避免標籤化 在歷史中看見歧異的能動性與身分認同
系列文章(下):
待續。
編輯:劉達寬
Cover photo Tech. Sgt. Erik Gudmundson on wikimed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