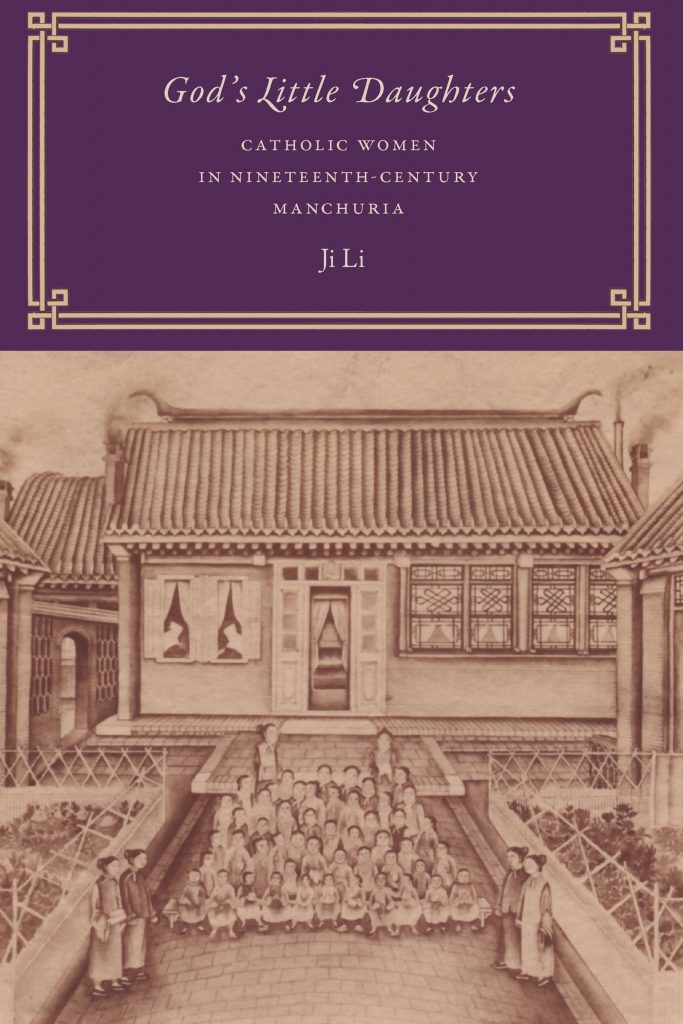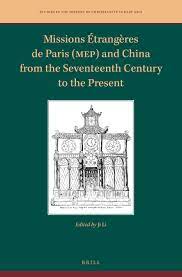談到制度嚴謹、階級分明傳統宗教,我們馬上想到的可能是保守而陳腐的印象,然而日常生活中的信者是怎麼看待他們的信仰?與傳教士如何互動?當代社會的宗教師與其訓練,看似與百年前隨西方帝國主義散布的教會傳教非常不同,但其實有著理解上共同的切入點?《時差 in-betweenness》第十二期播客從方方面面,談彌散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宗教,尤其是從歷史中人的觀點,去理解宗教生活化的樣貌;也從宗教師的實踐中,看待西方世俗社會的「宗教自由」如何與當代的多元價值互動。
【編按】本文內容來自《時差 in-betweenness》播客第十二期「宗教學:信仰,魔法,身份,權力」,C-Culture Zine獲《時差》授權刊登文字版。
主持人:
郭婷 (Guo Ting) 多倫多大學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對談人:
程曉文 (Hsiao-wen Cheng) 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副教授
李紀 (LI JI)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倪湛舸 (Zhange Ni) 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鄭利昕 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神務碩士 醫院宗教師
從制度性宗教的俗民經驗打破史學研究框架
李紀:我的第一本書God’s Little Daughters: Catholic Women in Nineteenth-Century Manchuria(《主的小女兒:十九世紀東北的天主教女性》),是非常傳統的歷史題目,講十九世紀法國天主教傳教團體在中國東北的發展。但是找到一些很有趣的材料,所以特別關注中國的幾個守貞女、天主教女性寫給法國神父的信,從這個角度進入研究,但研究結構還是蠻傳統的教會史。
第二本書是我後來編的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 (MEP) and China from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巴黎外方傳教會與中國》)。其實巴黎外方傳教會是一個很重要的團體,我們中學時講法國保教權、帝國主義侵略等歷史的主體。這些現代傳教士,在不平等條約下大批來到中國,但他們跟早期的利瑪竇相差很遠,大部分出身低微、文化水平沒有那麼高,到中國都是無名之輩。
編第二本書的時候,我找到一個傳教士的材料。他在東北的一個村子裡,就是我第一本書看到的那幾封信,所來自的中國東北小天主教村。雖然我自己第一本書沒有寫到這個村子,但我後來找到他們的後人。2010年左右,開始跨學科地去到村子裡,跟他們家的後人做了一些田野調查。其中他們家族有一個女孩,1948年進到瀋陽的修院,後來東北解放的時候跟著法國傳教士到了臺灣,定居臺中,我第一次見她是2012年,現在應該接近90歲了。慢慢我會覺得,雖然研究的是非常制度化的宗教,有嚴格的階級,但是當你進入民間生活,會發現好多事情跟你在書本上看到的或者你想像的教會體系是不同的,傳教士和中國教徒的關係是非常有趣的。
像第二本書找到的這個傳教士,他是義和團之前,1899年來到中國東北,然後一直到1948年共產黨解放東北之後,在一個意外當中,被一位教友因搶東西而殺害了,非常戲劇化。最有趣的是,他在這個村子待了27年,為了編一本中文的口語學習資料,記錄了9000多條當地村民的對話。歷史學家通常都處理文本,從文字上去想像、重構社會,而現在你不光看文字,還聽到聲音;這裡面有很多故事,而我要思考怎麼去解讀這些對話,因為它是用法語拼音來記錄當地方言。所以最開始我拿到材料的時候,其實不知道那是什麼。我覺得這對做歷史的人來說非常迷人,給我很大的衝擊是說,「什麼是天主教」的這個問題,對中國現代的這種天主教村裡面的教友,非常草根的普通人來說意味著什麼?教會意味著什麼?傳教士意味著什麼?
我很想突破我們保守落後的歷史學界那種帝國主義侵略的框架,我們學界經常是在這個框架裡去講傳教士。那我現在找到的材料是非常日常生活的,怎樣突破這個框架去講天主教在中國人普通生活裡的意義?它會打翻很多歷史學的架構。比如說我們總是把1949年看成一個斷裂,各種天翻地覆的社會變化,但是當你進入天主教村的時候,你會發現沒有這個斷裂。雖然表面上有很多衝擊,教堂被拆、被砸,他們個人也受到一些衝擊,但是跟剛才提到倪柝聲那種在上海大城市的家族,遭遇完全不一樣。
在那樣的底層農村也經歷這些運動,但是日常生活的延續性是非常明顯的,所以你會覺得歷史是凝固的。凝固不是說它一成不變,而是說那種連續性讓你覺得非常震驚而戲劇性。現在我的寫書,其實是把這些歷史和杜家(當時那幾封信是姓杜的小女生寫的)聯繫起來。我越來越覺得宗教學、彌散,包括楊慶堃(C.K. Yang)最早的那些理論性的東西,非常跨學科,讓我在想怎麼從傳教士、教會文本到日常生活;讓這種歷史研究方法、處理的主題和檔案,能跟當代新鮮的研究找到共性。
我們研究所同事宗樹人(David Palmer)領導一個很大的研究專案,他集合的團體是做各種有趣的宗教研究的,伊斯蘭、民間宗教、佛教,而我都是講教會、階級、天主教傳教,雖然不能否認這種結構,但我設法在這種結構底下看到共性。現在我想做的是找到不同的理論化角度,去探討「天主教在中國」。
以動態歷程替代靜態區分
郭婷:其實前面講到很多重要的點,不只是在學界內,在學界以外的日常生活中,我們認為什麼是保守、落後或固化,其實更重要的問題是這些偏見是怎麼來的?這種印象怎麼被塑造?這種所謂的偏見、保守性,或者是所謂的現代性是怎麼來的,怎麼得到體現?怎麼在各種交互中形成?
比如剛才曉文提到,基督教或是福音派,可能在臺灣或亞洲很多地方就是一個普通教會,並沒有在美國那種非常保守的狀態。但是在美國,如果你說你是福音派或基要派,就會有更多政治的面向。
程曉文:當然現在臺灣也有護家盟,最近幾年美國的福音派系統性地扶植臺灣的福音派,複製美國的模式。
郭婷: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保守派基督教在全球進行這樣一種連結,可能在早期天主教或基督新教的傳教時期,傳教士、亞洲的知識份子和普通民眾也在相互塑造彼此的形象。比如某些年代,基督教被認為是現代性的代表,和科學、理性、民主結合在一起,現在其實大家還是有這種印象。也有非常多政治保守的人物,他們在中國或亞洲語境下,又被認為是反抗極權、先進的自由派,因為人們所認識的基督教形象,是意識形態相互塑造成的。
最近有另外一本關於天主教的著作也翻譯成中文,是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寫的《傳教士的詛咒:一個華北村莊的全球史(1640–2000)》。 她也是研究教會史的歷史學家,也寫到華北的草根天主教徒,在大時代、革命概念下,被遺忘的普通信眾,他們對天主教的認識是什麼?對世界的想像是什麼?或者他們對所處環境的認識是什麼?可能不管官方或學界論述都經常遺忘他們,或是用另一種偏見、固化的想像為他們代言。所以李紀老師說到的不管是檔案或是後來田野訪問,都是非常寶貴的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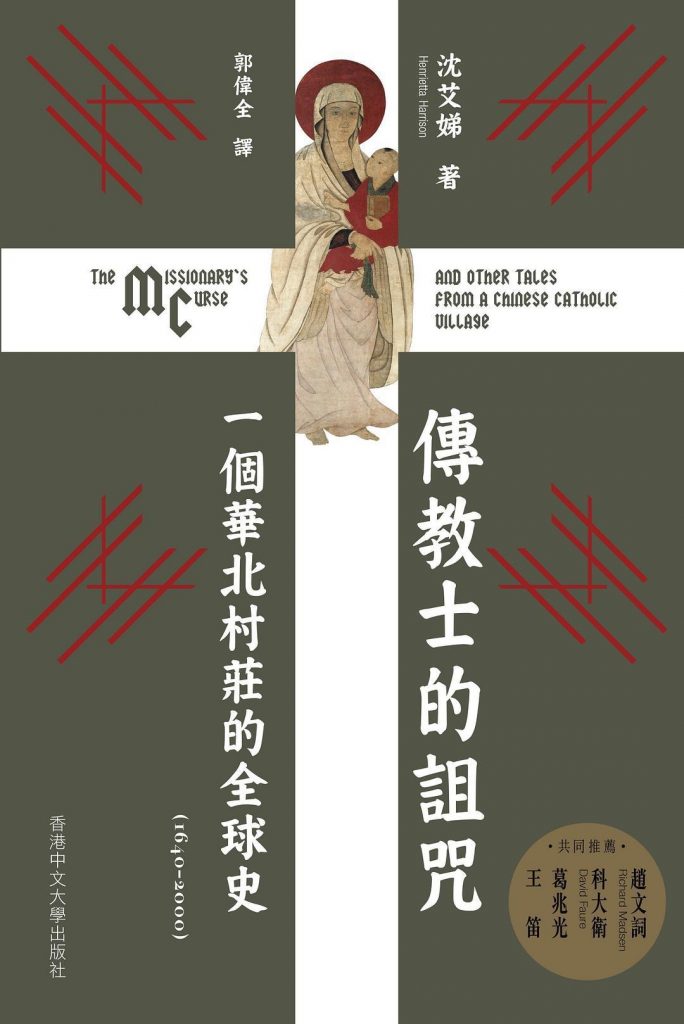
然後那利昕,想聽你來聊一下道學,或者說教牧訓練,和學界訓練有哪些不一樣?對你來說,你的訓練比較有趣的事情?
宗教師的實務訓練經驗與多元化
鄭利昕:我覺得最簡單的區別,就是我們神學院偏學術的碩士是兩年,而我們是三年,所以可以簡單理解為,多出來的一年就是分散在這三年內很多的實習、見習和偏向實踐類的課。比如像我自己第一年春天有去看守所見習,是非常短的見習。因為美國憲法保障所有人的宗教自由,也包括囚犯,所以在監獄或看守所有很多志願者團體。每周進去給受刑員帶各種宗教服務,現在也包括冥想、打坐等等,越來越普遍。我當時在一個老師帶領下,每兩週一次給一個女性看守所做類似傾訴小組、讀書小組的服務。有時候我們會帶詩歌或者是不同傳統的小篇章、小故事,大家坐在一起分享彼此的生活經驗,抱在一起哭一哭,然後再祈禱,這是第一年。
第二年的時候,會有一個非常長,四百小時的實習。每個人需要選一個實習場所,我選擇了一個佛教機構,在那邊進行一年的實習。還有一個你可以選擇在第一年暑假或第二年暑假進行的實習,我選擇在醫院做宗教師(chaplain)。這很有意思,對於很多基督教的未來牧師來說,他需要在醫院作為宗教師的實習學分。因為在上個世紀四、五十年代的時候,很多神學院的牧師發現,新來的神學院畢業生根本不知道如何去帶領一個教會,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做事務性工作,不知道如何與人打交道,可能只是讀了很多神學的東西,所以他們就慢慢成立了所謂的臨床宗教師訓練這一個項目。


無論在歐美國家的監獄、軍隊或醫院等公共機構,都將宗教服務視為基本安排
對很多基督教教派都是這樣,需要最低四百個小時的實習時間。醫院也有宗教師的需求,因此這樣的教育項目就開始了。在最近幾十年,宗教師、臨床宗教師,變成一個比較獨立的職業。如果你想成為職業宗教師,但是不在教會工作,你還需要再修三個學分,也就是一整年都要在醫院做這種所謂半工半讀。所以我接下來九月份要去的,就是這樣一個一年的學術項目。
回到我第二年暑假的醫院實習,做宗教師,還有一個很不一樣的地方。我們第二年會有一系列art of ministry的課程,比如怎麼樣做儀式,怎麼樣公共演講,怎樣展現領導力。核心是怎麼去帶領一個社群,去傾聽、做一個類似心理諮詢的角色。所以我們也學了很多心理諮詢理論、家庭治療,學了很多助人專業(helping profession)的基本理論,我也在社工學院上過幾門課。所以可以說在這個項目裡的人,一方面經歷了比較嚴格的宗教學碩士訓練,同時也上了包括社工、心理諮詢,甚至類似企業管理或非營利機構管理的課程。這樣等我們畢業的時候後就有足夠的專業,去做很實際的事務。
郭婷:這種宗教師的訓練、實踐,再到正式開始工作,這個職業還都是以基督教為背景嗎?
鄭利昕:可以這樣說,比如說在哈佛神學院,有一個項目叫做佛教宗教師,但這個項目可能只有幾年的歷史,非常新。然後我們芝大神學院也有說要專門安排一個專案,但還沒有到佛教宗教師這個程度,是慢慢在原來架構的基礎上,去往多宗教的方向演變,但是任何的演變都是有一個過程的。
比如說像教學大綱,要換成一個更加包容的課程設計,也需要時間。我在上學的過程中,也還是會聽到和感受到它原本是為基督教的目的來服務的。比如說公共演講,他就會假設你在佈道,而不是像佛教裡的講法,那是通過很不一樣的形式進行的。
我們的考核方式也還是針對一個非常具體的社會事件,要你給個二十分鐘的演講,老師在設計考核的時候,他腦子裡邊預設的還是基督教講道的形式。不可避免的問題就會是,不同宗教的人想像的儀式或公共演講能不能在這個課堂裡面表現出來。我相信之後這個項目設計之後也會演變得更加包容,但這會是一個比較長的過程了。
郭婷:你剛說到考核形式也挺有意思,這種考核也很美國,比較注重口頭表達能力。在學界,尤其宗教社會學,經常會討論說不管從信教人數或是基督教對公共生活的參與來說,相比於西歐或北歐來說,美國是相對比較基督教化的國家。這也體現在宗教師這個職業,不管在監獄或醫院,還是會預設需要照顧大家的信仰、靈性需求,採取宗教師形式來看護。這其實就是以前基督教牧師職責的一部分。如果我們看美劇,包括政法劇裡的宣誓這一套,其實也是美國在冷戰之後強調基督教對政治和社會生活的參與,成為美國國民性的體現。
說到宗教師,我記得在英國開會時遇過一位錫克教的宗教師,她是英國第一位錫克教宗教師,也是第一位女性宗教師。而且她是隨軍宗教師,要拿到這個工作必須和新兵一起訓練,所以她的體魄也非常強健。這也是改變的一部分。 想問問大家,你們在美國讀書的過程中,或者在觀察教學的課程設置裡面,是否感受到從基督教轉向對多元宗教更包容的一些改變?你們現在的研究和觀察,覺得宗教和美國社會生活的關係是怎麼樣的?
系列文章(上):
【時差】宗教學(一):當代宗教學培育場景 宗教師、跨領域和歷史學
【時差】宗教學(三):去標籤化的同時避免標籤化 在歷史中看見歧異的能動性與身分認同
系列文章(下):
待續。
編輯:劉達寬
Cover photo:1876年巴黎外方傳教會神父在貴州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