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們書寫時總是已運用著某種語言,有其文化脈絡也與日常的溝通不可分。我們是否清楚所說的是什麼?能夠透過語言反映現實,或者書寫只是虛構?預先設定類別、範疇,能框限住話語和書寫嗎?好比我們說有「知識性的語言」和「藝術性的語言」、有「中國文學」「英國文學」「日本文學」和「台灣文學」?文化是否已經現成存在,文學只是去描繪它?書寫者、轉譯者是否有一條保持自發、自覺地與文化的異質創造性同行的秘密路徑?種種問題在書寫時縈繞不去。C-Culture Zine本次邀請專長於當代法國哲學、哲學文學理論與批評以及美學的東海哲學系潘怡帆老師,分享她歷經哲學與文學洗滌,在書寫問題上的獨到觀察;本次訪談於疫情嚴峻時以線上視訊進行,透過虛擬談論虛構,攝影工作則於防疫規定鬆綁後完成,以身體性的交會提供補充。
楔子:以書寫挑戰「危險的對話」
海德格曾以他與手塚富雄的對話為基礎,書寫了〈從一次關於語言的對話而來——在一位日本人與一位探問者之間〉一文。文中提到日本電影其實是受歐洲美學洗鍊的表面日本,深層的日本只能在日本藝術中的能樂被經驗到,電影本身已經是歐洲語言,是在歐洲思維下的表現方式。日本人與探問者在對話之中發現了這種危險,亦即,我們所使用的語言有可能破壞我們所要表達的意義,為了進入到對方的語言脈絡,對話者勢必做出讓步,將自己的文化脈絡、思想背景化約到另一種語境之中,那麼,人們就未必能在對話之中達致真正的理解。
倘若對話的危險把我們推向如此的境地,我們要如何重新檢視我們用來交談的語言?人與人的對話是為了溝通,工具論的語言觀要求語言有固定的形式,並且只能對應到單一概念,這種語言觀忽略了事物的地位,因為事物在不同時空條件之下會以不同的樣貌顯現,進一步來說,工具論的語言觀讓我們在對話之中排除掉對話者的文化脈絡與思想背景。然而,現代科技似乎成功透過影像還原了某種思想脈絡,我們可以透過貼圖察覺某人的語氣,也可以在視訊畫面中關注對方的表情。雖然對話中化約式的思考在工具論語言觀中被推展極致,但我們好像還是能在另一種對話方式中發現對話者之間的狀態或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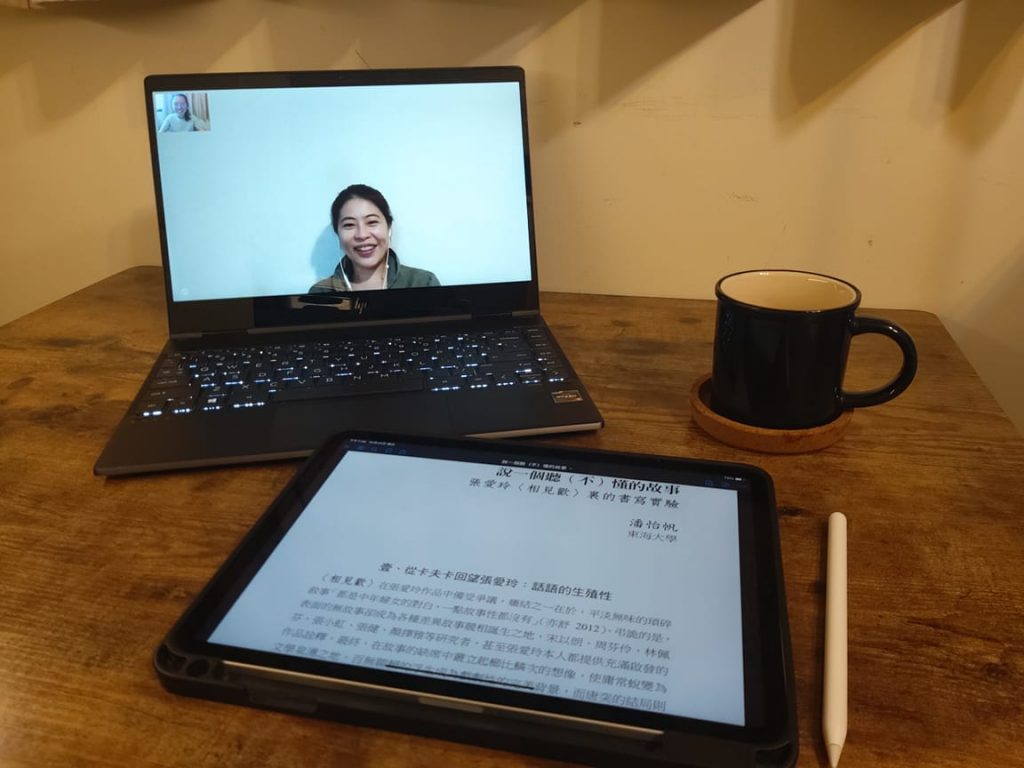
由於疫情警戒,各地大專仍採取遠距上課模式,本次訪談最終以視訊的方式完成。科技讓我們可以跨越空間限制,開啟「面對面」的對話,但勢必也讓我們忽略身體的厚度,被簡化成螢幕上的一張臉。我們不會得知對方是否因為過度焦躁而扭結了腳趾,也不會知道對方是否其實更關注畫面之外隨意走動的貓咪,我們只是在科技的幫助下,想像一個全心與我們對話的面容。
在新形式的溝通環境之下,人們能夠開啟什麼樣的對話呢?我們是否成功擺脫化約式的對話了呢?這也是本文的目標之一,除了紀錄與潘老師的對談,也重新在書寫實踐中挑戰書寫的界線。被轉換為文字的對話實際上也已化約了對話脈絡,如同先前提過的「對話的危險」,如實還原對話亦是不可能了。因此,本文意在成為某種延續對話的「回應」,試圖在書寫之中為對話打開新的軸線,並在新的軸線之中重新證明,所有被說出的話都是等待著回應,而非為了成為定義或成為化約其他可能的危險。
(潘怡帆老師目前於東海大學哲學系任教,下文將潘老師縮寫為「潘」,將訪問人鄭傑芳縮寫為「問」)
破題:「 語言跟我們的關係 」
問:潘老師參與過字母會的文學實驗,也寫過《論書寫:莫里斯.布朗肖思想中那不可言明的問題》、〈真文學及假書寫:博蘭,布朗肖的先驅者〉、〈說一個聽(不)懂的故事〉等圍繞著「書寫」進行深度思考的文章,想請問老師為甚麼會如此關注書寫問題呢?
潘:好,為甚麼關注書寫問題?應該這樣說,在二十世紀,語言或書寫變成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原因在於人類長久以來都用語言或書寫表達自己的思考,想方設法要逃離思想的侷限、陷阱或框架,從思考發展出後設思考或從思考的內容更往後推到構成思想內容的思想方法到底是甚麼。例如笛卡兒的「我思故我在」,或是亞里斯多德從物理學到物理學之後的形上學,或者是費希特的自我與非我的辯證,這些都在不斷地往外推,不斷地讓思想透過越界的方式走到框架之外,而這種努力無非都是為了使我們把自身的關懷看得更清楚。
但我們似乎從來沒有想過,我們用來表達思想的書寫或者是語言跟我們的關係是甚麼,確切的說,過去我們把書寫跟語言當作是表達思想的工作,但我們是不是曾經檢驗過這個工具它本身的特質是甚麼?是不是有想過「書寫是甚麼」的問題?假設我們從來沒有考慮過這一點,如何敢放心的把自己的思考交付給一個我們甚至不知道它是甚麼、也不知道能做甚麼的東西?
反過來說,如果我們曾經想過書寫是甚麼的問題,那我們馬上面臨範疇的問題:文學的書寫、哲學的書寫或者是數學、經濟、各種學科的書寫,這些書寫的意涵到底是不是一樣的?如果不是的話,那麼它們的分界線在哪?
如果我讀一篇文章需要先確認這文章到底是屬於哪個範疇的書寫,那這種透過範疇規約書寫的方式是否意味著書寫的界線其實不存在?更具體說,當傅柯在晚年提到「除了虛構,我甚麼都未曾書寫」的時候,他所說的「書寫」是否是我們都同意也認識的「書寫」呢?亦即,書寫等於虛構。這也是我個人為甚麼關注書寫的原因,因為我想要確切地知道,我用來表達的東西到底是甚麼?我要表達的那個東西,它到底會以或將以甚麼樣的方式被傳達。白話一點來講,我想確認的是:我到底知不知道自己正在講甚麼? 倘若哲學的核心在於傳遞、辯證或釐清思考,那我們就不可能不在意書寫的問題,正如同赫拉克利特很早就告訴我們的,「Logos」是話語也是道,這兩件事情其實是一樣的,釐清書寫是甚麼或關注書寫無非是為了關注「我的思考是甚麼」,並且是為了要理解我的思考以甚麼方式被傳送出去。

續篇:
【專訪潘怡帆】從一次有關虛擬虛構的對話而來:跨越真實與虛構的書寫(中)
【專訪潘怡帆】從一次有關虛擬虛構的對話而來:透過文學思考台灣(下)
延伸閱讀:
字母會側寫:流變為他者——我們還能寫怎樣的小說?
博客來-譯辯:班雅明與布朗肖
採訪、編輯:鄭傑芳
攝影:鄭傑芳
核稿:劉達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