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大華人文化主體性研究中心於 2019年舉辦「創傷與照顧:華人社會家庭脈絡下的思考」五場系列工作坊,主題涵括性侵倖存者、政治暴力受難者、罕見疾病及安寧療護等;透過邀請實務工作者進行經驗分享,與來自心理學、精神分析等領域的與會者對話,讓實務工作的議題與考量進入人文學科的視閾,深化對於華人文化脈絡下何為「照顧」的討論。
第二場工作坊「倫理的極限處境:從罕見疾病談世界照顧的樣態」於2019年7月舉辦,由東華大學諮商與臨床心理學系助理教授翁士恆、黏多醣症病友家長 · 罕見疾病基金會資深志工歐玲君與貝克式肌肉萎縮症病友家長顏秀鸞共同與談,透過罕病家屬的分享,從病理以外的觀點反思照顧的倫理。
如何陪伴受苦者走下去?
顏秀鸞談到兒子君志發病的經過,在學校有教跳繩的課程,兒子回來後她跟說:「媽媽我沒有辦法跳繩,但是我的同學他們都可以」,經過檢查,醫師診斷他患的是「貝克氏肌肉萎縮」,診斷過後孩子都發展跟活動能力看似正常,但到了國中時期退化的情況愈來愈明顯,顏秀鸞說自己如何從原來堅持各種學習活動到復健生活,慢慢接受兒子身體退化的現實,君志坐輪椅時的震驚以及病症在面對社會時的羞怯都還不是最難調適的,而是身體每兩個月一次的退化,做復健也難見益效,走到孩子高三的這個年紀,顏秀鸞經常面對這些害怕與掙扎。孩子退化的狀況就像一次次的刀割在心上。
顏秀鸞坦承這個病對君志和她影響甚鉅,他們甚至不太願意談論它,在病發當時,她是深感在幽暗的隧道中深感茫然。因為病症而帶來對未來的不確定感,也加重了生活動中本來會遇到的那些抉擇時的焦慮,比如高中選擇學科類組、復健是否要繼續等;身體能力和可能性的剝奪,不願讓家人擔憂的顧慮,君志經常把鬱悶和難過都封閉在自己心中。顏秀鸞說直到近來孩子愈來愈大愈成熟了,才比較願意表達,說出他心中的感謝。

聽完顏秀鸞的分享,翁士恆邀請工作坊的參與者提問、分享與討論。顏秀鸞的分享特別突顯了陪伴與照顧的困難,相對於維持著日常時間性的世界、人們在其中能計畫自己的未來的世界,罕見疾病的病友與其家庭面對著艱難的情況,有參與者回應說雖然秀鸞姐不見得可以用語言很清楚直接的講出來,但是從她的分享中卻已經將這樣的處境顯露出來,也就是當這些人從世界跌落了,這個世界的時間仍依然不停前進,如果是這樣,我們要怎樣在受苦的這條路上相互陪伴走下去?歐玲君以自己的經驗回應,那是沒有辦法控制的恐慌和無助,回想孩子住院的那段日子,台灣雖然已經在推廣安寧療護,其實還是很多人不知道什麼叫「安寧療護」,甚至還有很多醫生都覺得那就等於放棄醫療救護,他們不知道的是當人的生命走到最後,無論是病人或是家屬都需要有最後的尊嚴,換言之,在臨終的病床邊,適當地給在場的所有人得到最後的抒解,讓「生死兩相安」;理解安寧療護的意義時,玲君姐明白孩子住院受苦還有這樣特別的意義:讓醫護人員更了解,安寧療護的重要性、安寧療護不只是放棄醫療救護。
歐玲君也分享她在當罕病志工時遇過的令她欽佩的個案,她表示自從去當志工後,她覺得自己孩子受的苦並沒有那麼多,因為她的家庭支持力量是比較健全的,透過不同的生命接觸也讓她察覺──如果沒有溝通,很可能都只是我們的一廂情願,她以某個漸凍人家庭的情況為例,病友已經無法說話而且吞嚥困難,但還可以寫字,他強烈表達自己拒絕以插管的方式走完人生,於是邀請家人共同討論,在過程中說出自己的想法並達成共識,兩天後病人就走了,但他走得平安,家人也是安心的。這讓歐玲君體悟,我們以為的好未必是好,讓病人能自己選擇自己活著與離開的方式也很重要。
如何轉化別人看到的臉?
翁士恆老師藉此提到後現代思潮中,面對死亡時,心理治療發展出很多不同的進路,其中一個比較著名的學派是「建構取向」(constructivist approach)的哀傷治療,其重要概念就是:不是跟死去的人說「再見」,而是要說「哈囉」,因為亡者仍以不同的方式繼續存在,像這樣的思考最近開始在全世界、不管是輔導或者需要要面對死亡的領域等都在發酵。翁士恆進一步強調:如果能對這些開展更深入探討其意義與路徑,那應該能挖掘很多可能性,比如他自己就在不斷思考這些倫理極限處境中的溝通,如何在人與人的關係中發現意義,如他在歐玲君的行動中看到的,對於跟自己、跟孩子乃至世界的連結,和對意義的尋求,讓她的孩子並沒有被忘掉反而存在更多人的心中。翁士恆也向歐玲君提問,面對人們經常以悲憫或憐憫的情緒來對待受苦者與罕見疾病家庭,要如何去轉化這樣的態度,讓別人看到自己的不同面目?別人一定會悲憫你,那你的臉是怎麼轉換過來的?
歐玲君談到,推著孩子外出時,很難不招來異樣的眼光,因為孩子成熟的臉卻有著那麼嬌小的身軀,一定會引來別人的關注。回顧當時的情況,她表示在面對他人眼光時,她希望得到尊重,在別人看自己的孩子時,她會去搜尋對方的眼光跟他的眼神相對,也跟對方點頭微笑。她表示自己是在用身體語言試著告訴對方:
是的,這是我的孩子,我以他為榮。
那樣的行動會發酵,當對方感受到,他就會願意靠近,會走進蹲下和孩子說說話,孩子也接受到更多的關心與愛;也因為孩子確實感受到別人的關懷,他就也會給予家人和身邊的人回饋,這反過來增強了歐玲君自己的能量,也讓她更意識到,每個人的生命都有意義,只是我們有沒有願意正視與反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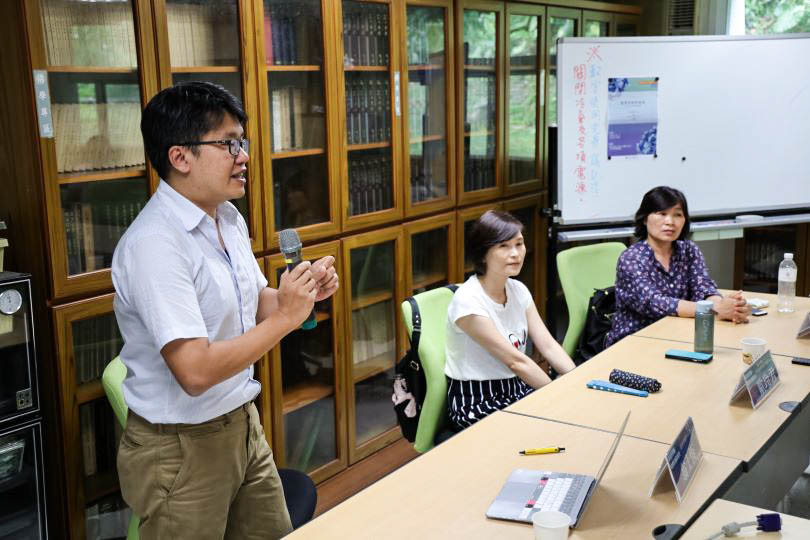
從受苦到倫理上的療癒
翁士恆回應說,在這樣艱難的處境裡,我們可以看到「媽媽」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但是在我們目前社會的處置裡面,不管是醫療也好、教育也好,我們常常會剝離媽媽的這個角色。當我們把「這個孩子」視為病人,把「這個媽媽」視為阻擋我處理疾病的人,我們就脫離了「媽媽」的這個角色,即當我們看到受苦中的孩子,我們自然會對他產生悲憫的臉孔,同時我們的悲憫臉孔有時也會切割孩子身邊媽媽原本的角色。
翁士恆指出,一個很清楚的路徑是,媽媽必須先站好她的位置,然後去說:「對,這是我孩子,我是他的媽媽」,然後才能透過這個的方向讓媽媽的位置可以出現。顏秀鸞分享說身為一個媽媽,最不想面對的就是孩子的死亡,遇到這樣疾病情境的時候,媽媽和孩子最大的問題就是「無奈」和「絕望」。翁士恆老師同理地回應說,我們永遠沒有辦法知道媽媽要承受的是多大的痛苦,那是完全無法想像的。所以這種「無法想像」的處境,似乎有一種「不可能性」在那裡,這種不可能性會把任何人推到完全無法使力的空無境地裡;在倫理的處境裡頭,這種處境就是極限的處境(boundary situations),它是由海德格(Heidegger, 1889-1976)跟雅士培(Jaspers, 1883-1969)在上一世紀所提出的重要概念,是「不可能做到」的處境,透過這些處境,媽媽們讓自己變成一個非凡的人,玲君姐已經走過了這個艱難階段,而秀鸞姐正在踏入。顏秀鸞分享,有時在孩子復健很辛苦的時候,她會告訴受苦中的孩子:謝謝你承受的這一切,我都看到了,這樣做好像能給彼此力量繼續走下去,也能讓彼此更靠近。
最後,翁士恆回歸到整個工作坊主題「倫理」與「照顧」上,我們設法要去理解倫理是怎麼一回事,那麼倫理中有沒有照顧的可能,當面對疾病的處境非常艱難時,照顧最終要堅持的是什麼,我們在家庭中、在關係中所要堅持的是什麼?現場有人回應,我們應該敏銳地察覺自己都在凋零中,藉此能彼此相惜。而談到「母親」的角色,她並不只是世俗倫理中互相交流的有施、有受的角色,而是純然的給予、是犧牲或愛的典範,從對母親角色的反思,我們或許就要重新思考罕病乃至臨終等極限處境的倫理,並不只是交互的倫理意涵,而是如同母親的角色這樣給予的倫理關係。

撰稿、編輯:劉達寬、曾雅麟
審閱:翁士恆
Cover photo by Matheus Ferrero on Unspla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