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離其所」後如何返回現實?哲學研究最終要探問的是什麼?是否不僅是書面經典,而是時代的「切膚之痛」、不可躲避的生命核心?中研院文哲所黃冠閔研究員,長年研究「主體」哲學,特別關注「非我」、環境與「自我」的關係,這些關注反映在他過往出版的《在想像的界域上:巴修拉詩學曼衍》與近年對史賓諾莎的研究中,彰顯其特殊的關懷:主體並非孤獨地思考而存在,而是屬於自然、與其他物種共同生活於宇宙之中;哲學需要如此根植於我們所生存的社會現實脈絡之中。
老師這幾年的研究主題似乎在有一些轉換或是轉變。您早年研究風景、場所等主題,到了《感通與迴盪》更多是倫理學問題的探討。而近年研究計畫中則更關注政治議題。這些轉變的脈絡是什麼?
黃:我在寫博士論文Schelling et la crise de la métaphysique (《謝林與形上學危機》)時,其中一個最核心的問題就是主體性。如果說費希特與黑格爾的主體性都較為朝向絕對的主體性、交互的主體性;那麼謝林在談主體性問題的時候,則是以自然哲學為重要的基底。以此框架來看當代哲學,會有一定的參照有效性,因為它不會如同現象學那般過於偏重意識主體的一端,而是更接近也更容許自然、空間、非人類的視角。
在辯證法式的思考底下,謝林哲學提供了一種看待世界、看待動態性發展的結構,這大概是我剛回國時的早期關注,一方面我希望能夠繼續研究謝林哲學,另一方面在與臺灣學界互動時,也有不同的需要,因此不斷集中於討論主體性。此外,同時我也發現法國哲學家巴修拉,對於「想像力」有著特別的處理,而「想像力」在主體性問題上也是一個相當重要的環節。
透過物質想像、四元素等等,巴修拉開展出與自然的對話,因此他的主體性並非單純是社會性的、人間性的,而是一種必須面對自然、宇宙的主體性。從這裡,進一步延伸到了所謂「場所」(lieu, place)的概念。「場所」作為廣義的空間概念,是不同於一般科學意義下同質性、無差別的“space”概念,而比較趨近於亞里斯多德、乃至於柏拉圖時代下對空間的想法,涉及到我們具體坐落的生存處境。
從主體性到場所、乃至於到風景的思路,就這樣貫串起來。主體性問題所涉及的,不只是人作為主體,還涉及「主體自我證成的判斷依據」,以及這種判斷依據來自哪裡?──這有兩重:(一)屬己的意志、或意識;(二)非己的──如謝林式、自然哲學式的看法。「主體性」是需要這兩重交錯,因為單一的自我封閉、自我重複的方式,是無法肯定主體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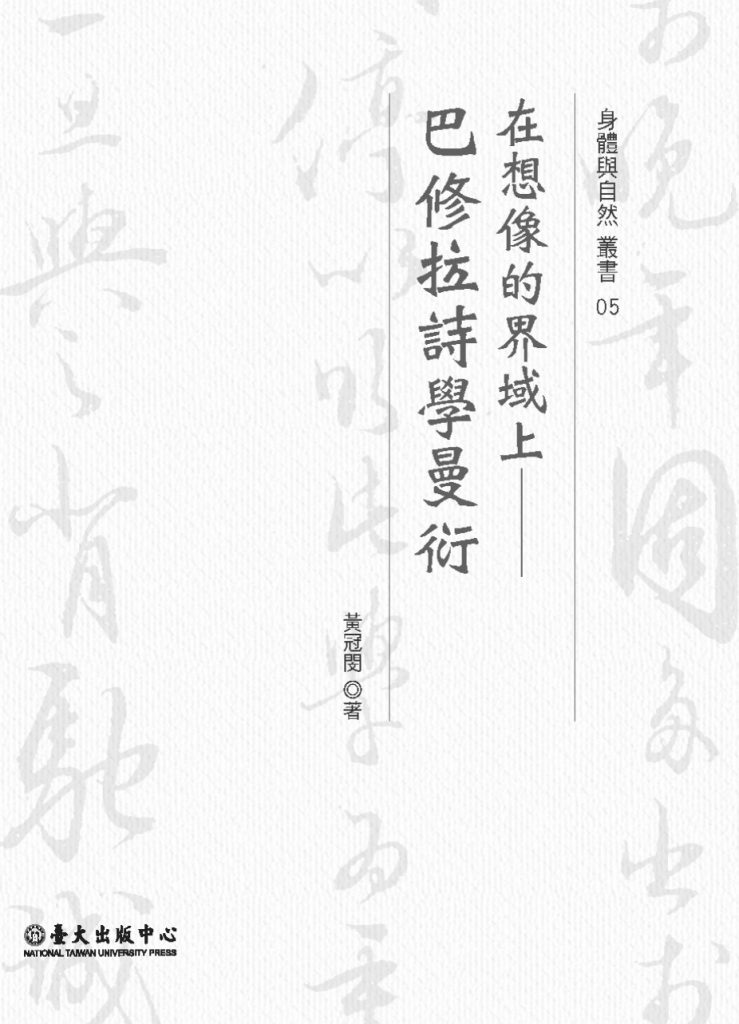
雖然巴修拉某些學生視他為唯物論者(materialist),但與其說他是唯物論或物質主義者,不如說他是一個宇宙性的思考者。我曾想從這個宇宙性思考者的角度去執行一個研究計劃,就是探討「Cosmopolitics」的另一層意義──雖然現在「Cosmopolitics」普遍被翻譯為「世界公民」、「世界主義」,但是它背後其實是一種「世界性政治」或「宇宙性政治」的觀點。
延續對非人視角、自然的關注,我也把目光放到史賓諾莎上。他的自然概念也涉及「affectus」的概念──我翻譯成「觸動」或者「感觸」,因為我希望保留它在現象學脈絡中與觸覺有關的意涵──它也與情感性、身體性的問題緊密連結,可以呼應到我討論唐君毅時所談到的「感通」,進而觸及倫理學的意涵。這是我仍在醞釀和發展的方向。
老師對很多哲學家,都帶有犀利的政治性批判目光,這似乎代表您有著比較強的現實關懷。是否可以在這方面做一點說明或是補充?
黃:這大概要分兩個層面。第一個層次是現實;第二個層次是現實當中所包括的政治性與社會性──我的研究構想是沿著社會性的方向,採用一種逆反於鄂蘭式的做法。
面對切膚之痛的現實
關於現實,未必只是政治現實,而是更廣義的:為什麼要做哲學?為什麼哲學在現實當中仍有它的餘地,或者必要性?
我的確是近年來才慢慢比較深入地體會到:我所曾經理解過的德國哲學跟法國哲學,是建立在我的不理解上──我對於「德國/法國哲學與其政治社會現實關係」的不理解。我是在這十多年來比較常跑歐洲,而對其現實的理解多一點點。我們在書本上很容易看到各種哲學派別或哲學家們彼此對立與鬥爭,但是我們很難從書本上看到這些概念背後的社會現實境況,以至於我們很容易輕易將之理解為觀念的、理論的鬥爭。然而,那背後嚴酷的社會脈動與現實,的確就像馬克思所描述的,具有一種強烈的物質性根據,緊密關聯著經濟與政治生活,關係到權力的凝聚、運用,以及治理性。由於時代更接近,我們從當代的哲學家可以更了解這種關係,像是德勒茲、德希達、傅柯、李歐塔所發明的許多哲學概念,基本上都與他們所在的社會脈絡緊密連動著。
這就對應到在臺灣,為什麼哲學創作相應地比較貧弱的問題:因為它沒有辦法對應到我們真正所處的現實。這也跟我們社會環境中的一種自動生產機制(auto production)有關──這種機制將「知識的、批判的、對應自身、認識自身的方式」隔離開來,而讓知識的層次無法進入現實、無法與現實結合。光是要意識到這一點,都需要對社會有更深度的認識。
所以,如果要維持哲學的創造力,除了學術的傳承──也就是嚴肅面對與解讀文本、面對歷史的理解、做概念的開展──之外;還必須要試著面對社會生活、面對實際的現實面。這攸關事情的呈顯:為什麼它在我們周遭、以那樣的方式出現?在因果性的理解之外,還必須涉入價值性判斷、以及情感性連結,這些東西都相互扣合。只有當我們的概念能夠深入到這些面向,找出當中能夠轉化、深化、創造概念的可能性時,這樣的哲學概念才會生根、才會有創造性,也才能滲透到每個人的心中。
關鍵在於,在現實中,可能總是有某些地方,會觸動到每一個人的實際生命──一個人所無法別過頭去的,就是他要面對的;我稱之為「切膚之痛」。那個「切膚之痛」,如果能夠轉化成一個哲學概念,就會有力量。因為承受到這種痛楚的人,會清楚地知道這種哲學理論不是空中樓閣,而是實際上有力量的東西。
哲學家的功能就在於:他既必須要來自於現實,又跟另外一個思想的世界相互交錯,並且投身其中,致力於在這些綿密的、交錯的結合當中提煉出有意義的概念、活的概念、與我們自己所生存的環境密切關聯的概念。
政治的社會性層面
另一個層次是關於政治本身。我的確有很長一段時間蠻關心政治性的問題,例如施特勞斯、洪席耶、阿岡本、鄂蘭。但我慢慢覺得可以從「社會性」這個面向著手。政治性的問題並非不重要,只是相對來說,「社會性」的議題仍有待開發。一來可以透過社會現象學的角度切入,二來我也關注儒家傳統的脈絡挖掘可能性。 我所謂的「社會性」層面──如果用林遠澤藉霍耐特(Axel Honneth)的角度所談的──比較像是黑格爾界定的「倫理性」(Sittlichkeit),而不只是主權的問題。在大家談臺灣問題的時候,經常拉高到「最終認同」的問題;但「社會性」也是現實的問題,並且經常是多文化性的,當我們面臨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他人或群體,總是需要面對、處理多元而異質的價值衝突,這都與更廣泛的「社會性」息息相關;而且這些問題經常是找不到答案的,需要花時間細細打磨。我認為透過回應這些情況,同樣能夠促進公民社會的討論、維繫與成長。

(photo by Andrew Leu on Unsplash)
專訪系列文章:
【專訪黃冠閔】學思歷程:「『不得其所』的不安,留下空間與開口」(一)
【專訪黃冠閔】漢學與哲學迴盪:「我們從來不是既成的自己,有待重建、發明」(三)
【專訪黃冠閔】世界哲學、跨文化哲學與臺灣哲學:「臺灣有一種時間與空間上的脆弱性」(四)
延伸閱讀:
【專訪楊儒賓(四)】儒學民主化在台灣:氣韻背後的政治共感
【創傷與照顧 1】照顧哲學芻議—療癒性的交談與回復性的共同關懷
【書評】《 疫病與社會的十個關鍵詞》:污名、隱喻與觀看自身之苦
採訪:李雨鍾、賴奕妏
編輯:賴奕妏、李雨鍾、劉達寬
校閱:黃冠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