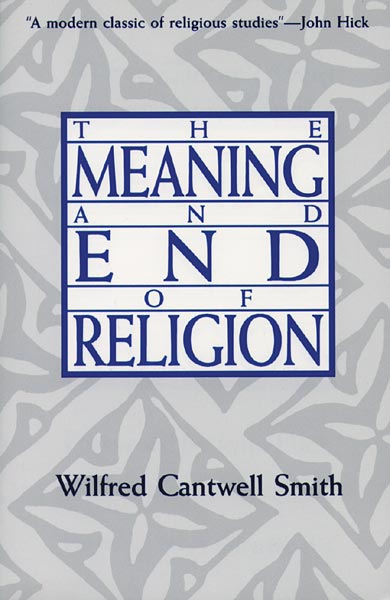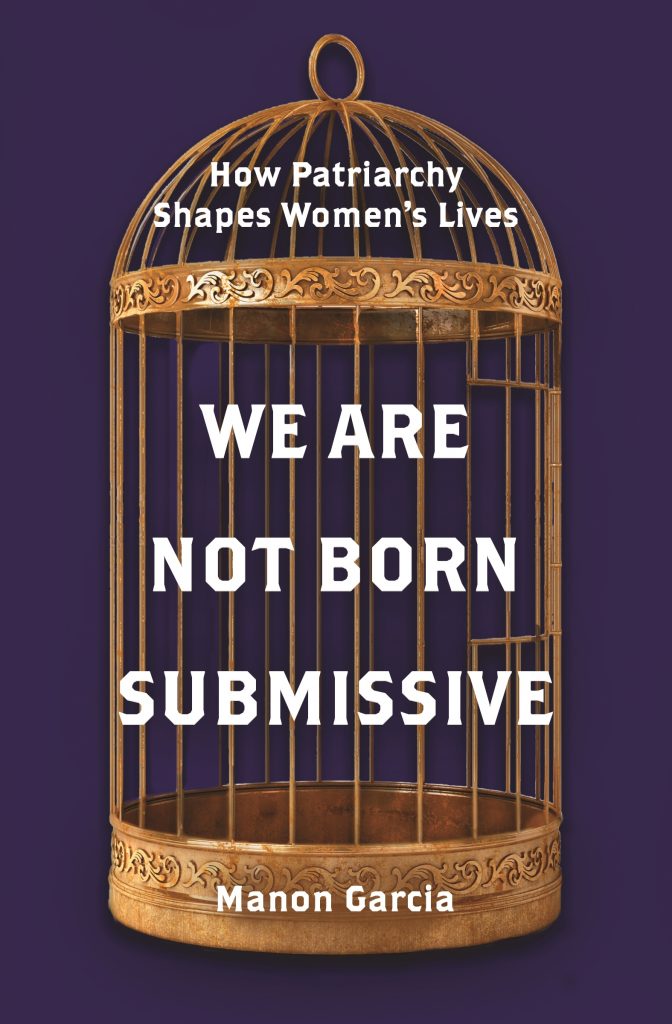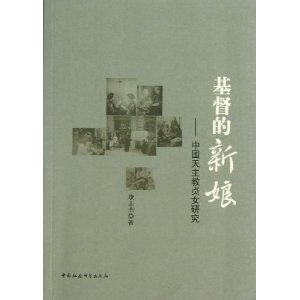重新以瀰漫、交織來看待宗教,宗教生活能提供我們理解當代世界的不同視野,鬆動不同群體之間本質化、僵化的相互理解,比如當我們發現某些動物也存在宗教情感與儀式,也會悲憫同伴,那麼就有可能在跳脫人類中心的同時,重新意識到宗教信仰的其他可能性。透過比丘尼、守貞女等女性群體在不同歷史脈絡中的活動,她們一方面是體制化宗教中的階級底層,但同時又保有自己與其他信徒的差異、多一些空間與學識,這使得我們必須以不同的方式理解她們的能動性,這也能進而幫助我們在面對當代多元族群、性別與權力的結構不平等時,能走出更多元的路。
【編按】本文內容來自《時差 in-betweenness》播客第十二期「宗教學:信仰,魔法,身份,權力」,C-Culture Zine獲《時差》授權刊登文字版。
主持人:
郭婷 (Guo Ting) 多倫多大學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對談人:
程曉文 (Hsiao-wen Cheng) 賓夕法尼亞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副教授
李紀 (LI JI) 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助理教授
倪湛舸 (Zhange Ni) 維吉尼亞理工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副教授
鄭利昕 芝加哥大學神學院神務碩士 醫院宗教師
宗教與當代世界:避免本質主義、宗教情感的作用
郭婷:剛剛很多大家說的我都非常贊同,曉文最後說到,我們如果重視信仰,或把信仰作為看待個體和社會的一個媒介時,能更加理解個人和群體的選擇,也更理解古代和當代的社會。這讓我想到最近的兩部電影,一部是講韓國移民的奧斯卡得獎電影Minari(台譯:《夢想之地》,原意水芹)。如果我們不帶著宗教稜鏡或視角去看這部電影的話,可能會覺得和李安早期的電影沒有太大的差別,都是講一代移民的故事。但其實這部電影除了與韓裔美國移民非常相關,也有非常強的宗教色彩。他們是基督徒,不過他們是以「亞裔移民」這個身份進入教會,那教會在美國社會意味著什麼?對移民意味著什麼?這部電影還連結到韓戰的,主角和幫助自己的美國白人之間的和解過程,也具有靈性意味。另外一部電影叫《茲山魚譜》(The Book of Fish),講述韓國儒士因為信仰天主教而受到驅逐的故事。如果帶著宗教的視角去看這些電影,可以看到非常多古代與當代社會的變遷。
還有剛才說到如果我們把宗教看成脫離日常生活、一個外在的範疇,也會產生「把宗教本質化」的危險,同時把世界其他人、他者化約成不變的東西,也包括把我們自己化約成一成不變的東西。比如說現在提到信教或者問說「你是不是有宗教信仰」,大家很容易聯想到基督徒,這其實就隱含著某種對立。因為曾經對很多基督徒來說,你沒有基督教信仰或有其他宗教信仰,就意味著你是迷信的。這種彼此的本質化、化約化,也是非常危險的。我們在做的很多工作,其實可能就是發現任何傳統、任何文化不斷變化的過程;也看出不同文化、傳統、人群之間如何持續互相影響、彼此塑造,這個在大家的研究裡面可能都有非常多的經驗。
剛才還提到今天我們怎麼去除新教對我們世界的塑造。其實曉文老師的一位同事Donovan Schaefer研究宗教情感,他想做的也是類似的工作。我們對宗教的概念受到基督教的影響,其實是殖民時代的產物,也把宗教和語言、理性、哲學概念聯繫在一起。而Schaefer則認為,宗教其實最重要的是一種情感。人有,動物也可以有。這就把宗教和語言的傳統分離開來,不只是去基督教化,其實也是去人類中心化。他談宗教情感的書Religious Affects: Animality, Evolution, and Power的開頭描寫了珍古德(Jane Goodall)觀看大猩猩的儀式,大猩猩會因為同伴去世聚在一起悼念,這種儀式其實就是宗教情感的體現。從情感或是宗教情感的角度來看,這是幫助我們重新思考宗教的一種方式,也對於宗教學幫助我們重新思考今天這個世界可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宗教學研究與當代世界:種族、性別與身分的刻板印象
郭婷:大家其實都提到女性主義研究以及東亞語境。因為我們是女性,或者因為我們是東亞人,也是我們會被問到是否具有宗教信仰的原因之一,大家就會覺得在你從事這個研究背後,有制度化宗教的關係,你應該是信仰者,才會進入這樣一個領域。或者在學界有另外一種分嶺,比如你是亞洲人就會研究亞洲宗教,你是女性就會研究女性主義或性別相關研究,通常是做自傳式的研究。這是為什麼有「宗教學」或者是「宗教與文化」這種科系或研究方法的存在非常重要。它其實也幫助我們去本質化,不再把宗教作為一種外在的東西來研究,不再把一個人、個體或者一個傳統本質化。
雖然後來有更多的發展與修正,但在一本經典作品《宗教的意義與終結》已經談到這些問題,如所謂「宗教」這個詞是怎麼來的?在這個詞出現之前我們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傳統、政治形態。該書也思考這些概念的機制化或正統化對今天這個世界的影響,這其實都是我覺得跟宗教相關研究非常重要的一點。這也是我想跟大家聊一下,宗教研究對於我們看待今天世界有些什麼影響?
比如最近一位法國白人女性學者Manon Garcia寫了一本新書We Are Not Born Submissive(《我們不是生來順從》)。她作為哲學家,受的完全是哲學訓練,討論的也是哲學概念,但這本書出版後,卻被打上「批判理論」、「女性主義」、「人類學」的標籤,但就不說她是哲學家。她覺得如果自己是白人男性的話,這種事情永遠不會發生,但因為她是女性,大家就不承認她和這種正統、經典、具有男性氣質的研究相關。在宗教學領域會不會遇到這樣的狀況?如我們剛剛說到宗教學怎麼挑戰傳統或修復傳統,不知道在種族、性別等相關面向上,我們教授的內容或是研究是否會有一些幫助?
程曉文:我想回應一下,但不知道我的回應是不是那麼切合。
郭婷:我記得你在《新書介紹》的訪談裡面講到,因為你讀書時期的訓練有liberal feminism的概念,後來遇到一位女法師的經驗?
程曉文:喔那段是我引用一本書。還是湛舸推薦我的,Nirmala S. Salgado的Buddhist Nuns and Gendered Practice: In Search of the Female Renunciant(《比丘尼和性別化的佛教實踐:尋找女性沙門》)。這本書在探討斯里蘭卡重建比丘尼傳統的運動,因為在南傳佛教中,比丘尼傳統斷掉了。原因是在佛教戒律裡,比丘和比丘尼都要受足戒,而針對比丘尼的條件要遠比於針對比丘的條件嚴格。關於比丘,只要有足夠人數的比丘來幫你受戒就可以完成;但比丘尼,則需要足夠人數的比丘加上足夠人數的比丘尼,才可以完成受戒。
所以如果在歷史上某個時刻,剛好湊不到足夠的比丘尼,就沒辦法產生下一個正式的比丘尼,這就變成了惡性循環,比丘尼因此絕種。可能在佛教傳到全球之後,結合女性主義的風潮,人們開始關注為什麼南傳佛教沒有比丘尼,就像關注天主教裡面為什麼沒有女性神職人員(priestess)一樣。這本書一方面講述全球政治的角力,另一方面,我自己非常喜歡的部分是,因為作者就是斯里蘭卡人,在當地進行長期的田野耕耘。從她的訪問裡,我們可以感覺出她跟這個地方關係非常密切,和這些人的訪談也非常深入。有時候人類學家說再多、再怎麼把自己的背景前景化,都不如這種深入對話給人的感覺。
在書的開始,她講述自己訪問一個剛受了足戒,成為比丘尼的前輩。那個前輩也長期參與恢復比丘尼傳統的運動。她問前輩說:你覺得自己是一個女性主義者(在當地語言裡類似womanism)嗎?而前輩卻很自然地回答她:我不是一個女性。作者當時覺得自己無法理解,她花了很多時間去想比丘尼的回答到底是什麼意思。後來作者意識到,可能比丘尼覺得自己跟一般女性不同。但是她們卻因為女性身份,導致要守的戒律和一般的比丘還有男性完全不一樣。明明收到這些限制,卻非常自然地認為自己不是女性。
宗教學研究與當代世界: 回應結構性的不平等
程曉文: 郭婷提到的我自己的經歷是,我以前在華大修Kyoko Tokuno [1] 老師的〝Women in Buddhism〞專題討論的時候,剛好有一個臺灣的比丘尼,也是教授到華大訪問,就請她來課堂上跟大家對談。我當時剛讀了很多liberal feminism的書,自詡為自由派女權主義鬥士,就問她對臺灣佛教機構或臺灣寺院裡的性別不平等怎麼看?她一直說沒有(這些問題),我們是「大丈夫」。於是我就問她,那你看到比你小20歲的比丘,要不要給他行禮、跟他鞠躬?
好像我們作為女性、作為有色人種的研究者,會比較受限制,似乎刻板印象認為只能做與自己身分相關的研究。我其實想要回應這個議題延伸出來的一件事情,比如在婦女史、性別史、種族主義研究,或者是LGBT的研究,這些原本被認為比較邊緣的研究,慢慢被一些披荊斬棘的研究者,包括女性、同性戀、有色人種打出一片天地後,一些「主流」研究者才開始關注這些研究。如果你是白人男性,你都可以做婦女史、做異性戀、同性戀研究等等,當然以美國來說做非裔美國人研究可能還是比較難。
我覺得郭婷提出的是大家都知道的問題,但真正的重點是要怎麼去回應。我們或許可以說,特定群體完全可以堅持做特定領域的研究,並且做得很好,但是如果仍存在制度性的結構不平等,要如何應對?我認為保障女性、少數群體在做少數、非主流研究裡的主體性的話語權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李紀:我簡短補充,其實在這種制度性的結構不平等下面,怎麼去看性別、種族這些問題?比如大家公認天主教的階級性很強,制度化相對完善。但在中國天主教體系下,歷史上有一個系統叫「守貞女」,跟修女不一樣。我有一篇小文章談過,女修會進入中國比較晚,所以有這樣的系統,而中國的守貞女,比如跟巴黎外方傳教會的體系,是十八世紀在四川開始的。所謂守貞女指的是:女性不想結婚,宣誓獨身,她們並沒有進入修會,還是住在家裡。但是規定她們要有自己的房間,還要遵守一套修規。
像我研究十九世紀的滿州、東北,發現他們也有一整套守貞女傳統。我最開始處理杜氏那三位女孩的書信,她們三位都是守貞女,住在家裡一輩子沒有結婚,參與教會的輔助工作。我到那裡做田野的時候,村裡人反而表示不知道守貞女這個名詞,當地人叫她們姑奶奶。他們就說杜家出好多姑奶奶、稱讚她們很厲害,她們的地位很高。她們會一點讀寫,因為要學藥理,還要做傳教的輔助工作。
天主教的貞女傳統由來已久,如羅馬時期誓守貞潔而殉教的則濟利亞(St. Cecilia)(左)
其實若從現在性別的角度去分析,或者講主體性、能動性;你會覺得不平等的制度下,這給她們一個自己的空間,而也有很多可以去延展、討論的。一開始我只發現三封信,但一直對這個議題保持關注。後來在巴黎的遣使會、別的修會裡面,也發現了好多守貞女或修女寫給神父的信,我也還在收集。雖然歷史情境跟現代不一樣,但我們可以思考如何去理解結構和個人的關係。作為歷史學家,我們都要處理歷史脈絡,進入歷史脈絡就變得複雜起來;作為研究者,我在處理文檔的時候,會發現歷史中的男性和女性都很複雜。他們之間的互動未必像我們所想像的那樣,好像在一個制度性不平等下,天主教女性就一定是其中的最底層。可能不同情境的發現,能提供一些新的看法。
系列文章(上):
【時差】宗教學(一):當代宗教學培育場景 宗教師、跨領域和歷史學
【時差】宗教學(二):看見生活中的宗教 農村人眼中的天主教與漸趨多元的宗教師訓練
【時差】宗教學(三):去標籤化的同時避免標籤化 在歷史中看見歧異的能動性與身分認同
系列文章(下):
【時差】宗教學(五):跨越性別與「正常」的疆域 領導力、網路文學和前現代醫療
【時差】宗教學(六):信科學也信神水?巫的日常好比水電工? 宗教作為對知識體制的批判
延伸閱讀:
【書評】宗教與暴力:讀《僧黌與僧兵:佛教、社會及政治的互塑》
[1] Kyoko Tokuno教授方於今年九月底過世。訃聞:https://jsis.washington.edu/news/in-memoriam-kyoko-tokuno-1944-2021/ 。
編輯:劉達寬
Cover photo by Photo Dharma on wikimedia